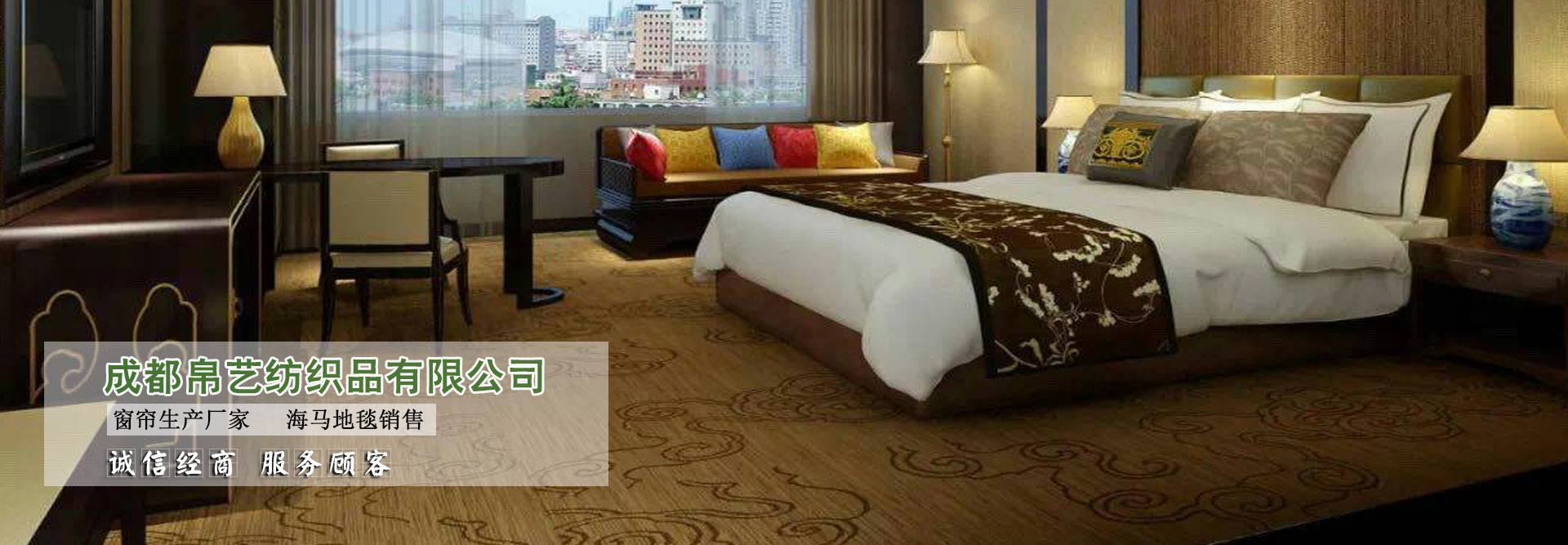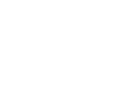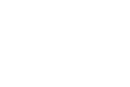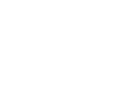时间: 2024-08-30 04:52:05 | 作者: 新闻中心
在阿尔泰山深处的万顷林海之中,哈纳斯湖静静地蜿蜒在山谷中。生活在这里的是两千多图瓦人,他们是我国北方古老游牧民族的一支,有不同于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:操突厥语、住木刻楞房屋、靠放牧和采集为生哈纳斯湖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圣湖。然而,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现代文明的冲击,他们的古老文化正面临着消失的命运。
从乌鲁木齐前往哈纳斯湖的途中,阿尔泰山沿路的风光已经让我心醉。成片一望无际的草原,星星点点的毡房,只要遇到牧群,从城里来旅游的年轻人就会兴奋得大叫。越往北走,景色变化越丰富,雪山,森林,高原美景现在眼前。在新疆工作的同学说哈纳斯是北疆最美丽的地方,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。
到了哈纳斯山庄,已是傍晚时分。一天的路程因为有秀色做伴,也不觉得十分疲惫。晚饭过后,天很快黑了下来。在山庄一块空旷的草地上席地而坐,因缀满繁星而清澈明亮的天空就在眼前,满天的星斗离我如此之近,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。
一夜好眠,醒来的时候天色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,清晨金色的阳光是摄影师们拍摄风光的最好时机,我已经迫不及待前往圣湖哈纳斯了。哈纳斯的清晨美得像梦,晨雾笼罩在森林、河谷之上,被清风吹拂,变成了有生命的精灵,自由地穿梭在湖面,游戏在树林之间。有的就在我的身边飞过,我伸手以为抓住了,却消失在指尖。等到清晨的第一道阳光穿过云端的雪山照耀在哈纳斯湖面上时,晨雾精灵们才从湖面散开,奔到苍翠的山峦之间,为我揭开哈纳斯湖的面纱。
等我登上哈纳斯湖最高的山峰,晨雾已随阳光散去。坐在观鱼亭里,可以俯瞰到哈纳斯湖的全貌,雄伟高大的青山现在眼前,苍翠的湖面和远山浑然一体,远处能看见白雪皑皑的友谊峰。湖中时不时有快艇划开水面,在哈纳斯湖上留下一道道水纹。我也迫不及待地从山上下来,坐上了游船让自己在湖面上漂泊。哈纳斯湖水深1800米,站在快艇之上,听着人们说着各种版本的湖怪传说,望着脚下碧绿神秘的湖水,不由得有一种幻觉,仿佛那古老的湖怪就在这快艇之下,准备冲出水面让我们见识一下它的真面目。
月亮湾令我此行最难忘,不同于卧龙湾河水蛟龙般的湍急,不似神仙湾的静匿,它弯弯的河道上那巨大的浅滩是神仙流连忘返留下的足迹,月牙儿般的沙滩卧在河道上,河水里倒映着两岸迤逦的风光。在阳光的照耀下,河面泛起彩色的斑斓,像是一道彩虹不小心从空中跌落,在这里汇聚成了世上最难忘的色彩。见到这样的美景,我的哈纳斯湖之行没有遗憾。
哈纳斯湖畔的图瓦人是一个神秘的族群,外界对他们的历史了解得很少。有关这些图瓦人的来源,查阅的资料往往会用“据说”、“传说”之类模糊的字眼。要了解这个神秘的民族,距离哈纳斯湖畔60公里远的禾木村是最好的去处,这个村落保留着最原始的图瓦人民族传统。来到禾木村,首先进入我视野的就是那一栋栋、一片片的木刻楞房屋和成群结队的牧群,房屋和牧群与高山、森林、草地、蓝天白云结合在一起,构成这里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。
禾木村北侧的图瓦人放牧点吉百岭是不可错过的风光。此刻正是秋季,牧民们把羊群从高山上的牧场赶下来,准备在这里度过一年中漫长的冬季。此刻的吉百岭水草丰美,许多地方的野草都长得没腰深。经过一个夏天高山上肥沃牧草的喂养,牧群已经膘肥体壮了。成群的牛、马、羊在这里自由自在地觅食,却难得看到图瓦人的踪迹。
走了一段路,一座小山脚下有泉水的地方终于看到了图瓦人的牧点,只有一栋木刻楞房屋和两顶蒙古包,距住处不远的地方还有成堆的冬贮草。男人们这样一个时间段早就已经上山采松子去了,这里秋天的松子皮薄、粒大、果香,深受远道而来游客们的欢迎。在游客多的时候卖个好价钱,也成了图瓦人家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。
走进蒙古包,一位叫郭柯的老大娘接待了我们。老人家今年已经85岁了,共有8个儿女,如今她和大儿子一同生活,其他的子女都居住在禾木村的定居点上。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,她拿出了图瓦人最好的食物招待我们。吃着咧巴,喝着奶酒,听郭柯大娘为我们介绍他们的生活情况。
图瓦人放牧已有几百年的历史,但与其他的地方不一样,他们的牲畜种类以牛、马等大牲畜为主。哈纳斯湖区冬季雪大,羊无法扒开积雪觅食,所以只有少数的山羊和绵羊作为肉食。禾木村的图瓦人原来一直是靠狩猎和捕鱼为生,为保护哈纳斯的生态环境,如今图瓦人已经停止狩猎和捕鱼了,他们大多以放牧为生。生活在定居点以后,转场放牧的图瓦人少了,一般都在村子的附近放养他们的牧群。当地饲草资源丰富、贮存较为方便,天气不好,干脆就把牲畜圈起来,人工投放草料。除了牛羊,图瓦人还饲养马鹿,马鹿是从山上捕捉的,没有人工繁育的经历。郭柯大娘带我们去看他们家的马鹿,它的个头有毛驴大小,野性十足,见人就用角顶,我们都不敢靠近。饲养马鹿主要是生产马鹿茸,每公斤可卖到1500元,一只七八岁的成年马鹿每年可产七八公斤。有了客观的经济效益,野生马鹿资源也在近两年锐减,饲养马鹿越来越困难。
生活在禾木村的图瓦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,现在当地的图瓦学校教学用的都是标准的蒙古文。听说原苏联和蒙古创立了图瓦文字,用斯拉夫字母书写,可以互相沟通。哈纳斯湖区的图瓦人如今用的都是蒙古文字母,无法与国外的图瓦人沟通。这里的图瓦人虽没本民族的文字,但民族语言却完整地保留下来。在这里,我见到的图瓦人不分男女老幼,几乎人人会讲图瓦语,并且一直是作为本民族的第一语言,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。
听当地人介绍,图瓦语既有部分哈萨克语,也有一部分类似蒙古语,其中也不乏一些本族群自己创造的语言。最有意义的是,在图瓦人的语言中还有许多突厥语成分,是民族学专家研究突厥语的“活化石”。
图瓦人作为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,在公元六世纪至八世纪的两百年中,一直被强大的突厥汗国统治,语言文化也深受其影响。我想图瓦人的突厥语言之所以能保留下来,与当地交通环境闭塞、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不无关系。哈纳斯位于高原深山,路远人稀,至今不通公共汽车,每年有七个月大雪封山,图瓦人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,许多人几乎一生都没出过大山。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,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十分缓慢,我所到的禾木村许多人家温饱都没完全解决,基本上没有任何文化娱乐设施,和外界的交流也很少,绝大部分学生因语言关系也只能上到高中。哈纳斯当地也没有蒙古人,蒙古语的交流仅限于学校的课堂上。图瓦语与蒙古语虽然同属一个语系,但并不同源,音位系统、语言结构、基本词汇的差异很大,图瓦人学蒙古语,如同学一门外语一样,很难形成气候和氛围,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进了图瓦语的保存。
遗憾的是,我不懂图瓦语,也不懂与图瓦语相关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,无法与当地的图瓦人交谈。面对淳朴善良而又热情的图瓦人,我只能用微笑和他们交流。由于图瓦人不是一个独立民族,许多专家学者不愿涉足这样的领域。我希望社会各界对图瓦人的文化研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,使图瓦文化早日走出深山,为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增添新的光辉一页。
...![{_CFG[site_title]}](/ms/static/picture/20181126010605377.jpg)
![{_CFG[site_title]}](/ms/static/picture/20181126010634169.jpg)